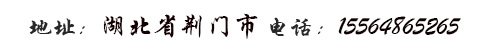民间故事绣花鞋奇案富家公子引诱良家女,
|
白癜风该怎么治 http://m.39.net/pf/a_6159813.html 明弘治年间,浙江杭州府有一个少年公子,姓柳,单名一个欢字,父母早亡,留下巨额遗产,落得他一人受用。 正所谓“饱暖思淫欲”,柳欢坐拥百万家私,成日只在烟花柳巷、舞榭歌台胡混度日。 人长得帅气,且出手阔绰,一干青楼女子,那个不喜爱? 个个极尽奉承之能事,将他恭维得神魂颠倒,乐不思蜀,连家也不怎么回。 妻子劝谏几次无果后,也就随他去了。 这天,春光明媚,有那些平时结交的朋友,差人来请,邀他去湖上划船游玩。 柳欢欣然愿往,换了一身华丽衣衫,手执一柄书画扇子,唤了随身仆童跟着,径直往钱塘门去了。 路过关子巷时,忽然抬头看见临街楼上,有个女子正揭开窗帘,往外倒洗脸水。 柳欢看得分明,当下只觉得身子酥麻,行动不得,心道:“世间竟有如此标志的人儿!” 想那柳欢也是久经花场的人,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?如是一般美女,怎会如此失态,可见楼上女子,天下罕有。 虽有一瞬失魂落魄,但毕竟是风月场老手,当下立定身子,假意咳嗽一声。 那女子将水倒了,正欲放下帘子,听得有人咳嗽,果然往下观看,一眼瞧见是个美貌少年,风度翩翩。 四目相对,那女子含羞带笑,柳欢越发魂不附体,恨不得肋生双翅,立即飞到楼上,一亲芳泽。 两人正眉目传情,偶2有人路过,只得收回目光,假意走了几步。 等路人行得远了,又转回来再看,女子已放下帘子进屋了。 心有不甘,在原地站了半晌,仍然没女子踪影。 只得暗中记下地址,盘算明日再来打探,之后才一步一挪,去赴西湖之约。 出了钱塘门,登上游船,那一堆朋友已经等候多时,见他上船,全都走到船头相迎。 寒暄过后,命船家开船,向湖心驶去,但见堤上桃花含笑,柳叶舒眉,往来踏青之人,纷纷如蚁。 有诗为证:出外青山楼外楼,西湖歌舞几时休?暖风熏得游人醉,错把杭州作汴州。 且说柳欢一船人,都是喜好风月之辈,早安排了青楼女子作陪,游船在湖上缓缓行驶,众人尽兴饮酒,弹唱奏乐。 反倒是柳欢一反常态,托腮呆想,兴味索然,全不像出来游春。 众人不解,问其缘故,柳欢含糊其辞,不愿多说。 朋友中有好事之人,假意责怪作陪的青楼女子,说她们怠慢了柳公子,使他不乐。 当下便有娇娇、翠翠、红红等人,一拥而上来缠他,劝他饮酒,推辞不过,敷衍了一会,寻了个借口,与众人辞别。 见他无甚兴致,众人亦不强留。 上岸进了钱塘门,又从关子巷经过,到那楼下,假意咳嗽一声,楼上并无动静。 兀自不死心,在巷子里来回走了几次,嗓子都要咳哑了,那随身童子便劝他:“公子,在此逗留过久,招人怀疑!还是明天再来吧!” 柳欢无奈,只得依言,悻悻然回到家里,第二天到附近打听,得知那女子乃是潘家独女,年方十八,芳名潘喜儿。 只是潘父借着与一户官宦人家有些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,在地方上作威作福,专干一些诈人钱财,骗人酒食的勾当,地方上人家,又怕又恨,背地里都叫他潘杀星,是个赖皮刁钻的主儿。 柳欢将打听来的消息,暗暗记在心里,不知不觉又走到那楼下,恰好看见潘喜儿临窗远望,顿时欣喜不已,目不转睛仰头凝视。 喜儿感受到炽热的目光,低头看到柳欢,也暗中高兴,两人眉目传情,彼此心照。 此后,柳欢时常来到楼下,以咳嗽为号,喜儿自会到窗口与他相见,眉来眼去,两情甚浓,只是苦于只能远观,不能亲近。 这天晚上,皓月当空,柳欢趁着月色,独自一人来到潘喜儿楼下。 见喜儿正卷起帘子,倚窗望月,轻轻咳嗽了一声,喜儿会意,微笑视之。 柳欢心旌荡漾,从袖中摸出一条红绫汗巾,结了个同心结,往楼上扔去。 喜儿双手来接,不偏不倚,正好落在手心,就着月光仔细看了,小心收在袖子里,弯腰脱下一只绣花鞋,丟下楼来。 柳欢得了鞋,拿在手中把玩,爱不释手,这时喜儿听到父母呼唤,关窗回到屋里。 将鞋儿贴胸收好后,回家径直进了书房,又拿出来在灯下赏玩,果然是金莲一瓣,爱慕之心更甚。 是夜躺在床上寻思:“如今这般,只得饱个眼福,得找个人与她传信,设法上得楼去才好!” 左思右算,也没什么主意,直到夜深,才勉强睡去。 第二天,带了些银子,走到潘家附近,寻了个地方坐下,盯着潘家大门,看有什么人来往进出,也好借机行事。 事有凑巧,没过一会,只见一个老婆子,手提着个小竹篮,进潘家去了。 约过半个时辰,才见这老婆子出来。 柳欢定睛一瞧,却是认得的,是那卖花的陆婆,就住在关子巷口,平时借着卖花,时常做媒作保,专业的马泊六(指撮合男女搞不正当关系的人)。 当下柳欢将陆婆叫住,闲扯了几句,借口有事商量,将陆婆请到一个酒楼,寻了个包间坐下。 要了一桌子酒菜,将酒保打发下去,把包间门关了,亲自斟酒与陆婆说:“有一事要劳烦,只怕你也难办到,若要是做成了,自有厚礼相赠!” 那婆子知道柳欢向来阔绰,能给他办事,自然求之不得,当下夸口:“不是老身自夸,任公子有什么疑难事体,交给老身,保管能办得妥妥贴贴,公子有事尽管吩咐!” “如此甚好!”将身子往前一凑,低声对陆婆说:“刚你去的潘家,我与那潘喜儿彼此有意,但苦于没有个传信的,知道你和她家相熟,特来相求,烦你给通个信,若能设法让我见上一面,必有重谢。先奉上十两白银,事成之后,还有十两。” 说完便去袖里摸出两个大锭,放在桌上。虽说见了银子两眼发光,但这陆婆却不露声色,缓缓开口:“潘家喜儿,平常见她端端正正,还是个黄花闺女,不像是个要胡来的人,怎会着了你的道儿?” 柳欢便把如何遇见,以及月夜赠鞋的事,细细说了一遍。 听后,陆婆连连叹息,口中说道:“这件事难办啊!” “有何难处!”柳欢忙问。 “他家的老子,那个潘杀星是个厉害人物,夫妻二人守着女儿,寸步不离,一家三口住在一起,也没个外人,门户谨慎,早关迟开,如何进得去他家?此事老身不敢应承。” “你刚才还夸下海口,现在说这么多,想必是嫌我谢礼微薄,故意刁难?总之,我不管那么多,此事定要你去办成,至于谢礼,我再给你加一倍。” 当下又掏出十两银子,丟在桌上。 自古“财帛动人心”,陆婆看着桌上的雪花银,眼中早已冒出火来,只是强行按捺住伸手去拿的冲动,想了想才说:“既然公子如此看中,若老身只是一味推辞,倒是不识抬举了。此事老身必定竭力图谋,成与不成,还得看你二人缘分。只是事先说明,成了自然皆大欢喜,倘若不成,公子休得归罪老身。至于这银子,暂且留在公子这里,等事情有了眉目,再来领赏。倒是喜儿给你的鞋儿,要拿来给我,好去做个话头。” “你若不收银子,我怎么能放心!”柳欢说罢,将银子往前一推。 陆婆见状,假意勉强收了,把银两揣到袖子里,心中暗喜。 柳欢又从胸口取出那只绣花鞋儿,看了又看后,才小心翼翼递给陆婆。 事情商定以毕,两人吃了些酒菜,临别时,陆婆又啰嗦了几句:“公子,此事只能徐徐图之,切不可操之过急,若限期限日,老身就不敢奉命了。” 柳欢有求于人,自然不好多说,只让她尽心去办就是了。 过了两天,早饭过后,潘父出门去了,喜儿在楼上,拿出柳欢扔给她的那条汗巾把玩,心想那翩翩公子,不知姓甚名谁,何处人士? 正独自儿坐在窗边烦恼,忽然听得有人说话,忙将汗巾藏了,走到胡梯边看时,见是卖花的陆婆,与母亲一道上楼来了。 陆婆热情招呼喜儿:“我昨天得了些新样好花型,特地送来给你瞧瞧。” 说罢从竹篮中取出一朵,递给她看。 喜儿接过来,细细观看,口中夸道:“果真漂亮!” 陆婆又取出一朵来,递与潘母,嘴里扯一些闲话后,说:“大娘,有热茶么?今早吃得咸了,口渴难耐,冒昧相求一碗。” 潘母一拍脑门,有些不好意思:“只顾着看花了,连茶都忘记给你泡,你且先和喜儿在这看花,我这就去烧茶!” 说罢,往楼下去了。 潘母走后,陆婆将花整理好,从袖中摸出一个红绸包儿,放在篮子里。 喜儿少女心性,以为是什么特别样式,问陆婆:“这包的是什么?” 陆婆故作神秘:“这是一件要紧的东西,你看不得的。” “怎么看不得?我偏要看。”喜儿说着就伸手去拿,陆婆假意阻拦,喊着:“决不能给你看!” 却是故意放了个空,早让喜儿一把抢到手中,打开看时,认得是那夜赠与楼下公子的绣花鞋儿,当下羞得满面通红。 陆婆趁她失神,劈手夺过来,装作愤怒:“别人的东西,怎么这般乱抢!” “切,只是一只鞋儿,我道是什么好东西,还弄个绸缎包着,搞得像个宝一样,有什么看不得的。” 喜儿也装无知。 陆婆瞅着她,戏谑道:“话是这么说,但你却不知道,有个少年公子,把这只鞋儿当成性命一般,爱惜备至,非要让我到处寻访另一只,说是要配成一对儿才好呢!” 喜儿自是聪慧之人,识得陆婆子是受那人之托来传信,心中暗喜,便去取出另一只来,笑道:“我这里有一只,正好与他配个对儿。” 当下两人也就不再藏着掖着,喜儿便问陆婆柳欢的情况。 “那公子叫柳欢,家中有百万家私,为人极是温柔体贴,自从见过你后,日夜牵肠挂肚,废寝忘食,不知在哪里打听到我与你家相熟,特央我来传信。你可有法子,放他进来?” “你是晓得我爹厉害的,门户看管甚严,就连夜间我熄灯睡了,还要端着烛台来看一次,方才下楼歇息,哪有什么办法!” 说完一双凤眼盯着陆婆,意思就是:你要有办法,就赶紧说出来。 “不妨事!老婆子有计在此。” 果然,陆婆早有计划,当下教喜儿。 “你晚上早点睡,等你爹上楼查看过后,悄悄起来,听到楼下咳嗽为号,拿几张布条接到一起,垂到楼下,待那公子扯住攀爬上来,自可相见。只是切记,至多到五更时分,定要速速离去,不可挽留。如此便神不知鬼不觉,往来百年也无人知晓。” 喜儿用心听了,拜谢不止,约好明晚依计行事,陆婆又要了另一只鞋儿,当成回信。 喜儿叮嘱:“这对你鞋儿拿去给他为信,明晚来时,让他依旧带来还我。” 商量完毕,就听得潘母上楼,两人止住话题,陆婆把鞋儿收在袖中藏好。 饮了茶,聊了些闲话,提了竹篮,起身告辞。 从潘家出来后,陆婆心情愉快,暗想这银子赚得实在轻松,一路哼着曲儿,径直往柳家去了。 哪知到了柳家,柳欢人却不在,两人所约之事,自不能告知他人,是以只说上门卖花。 柳欢的浑家,与家中一干妇女,将陆婆的花买了个干净。 逗留了一会儿,柳欢迟迟不归,陆婆只得起身作别,心想等明天一早来通知,也并不碍事。 回到家时,恰好儿子要杀猪,因帮忙的副手有事外出,正在那里焦躁不堪,见了陆婆,便唤她:“来得极好!帮我拉一下猪儿。” 陆婆的儿子叫陆大胆,是个屠夫,在家门前杀猪卖肉,平时酗酒斗殴,是个十足的凶徒,发作起来时,连自家亲娘都要教训几拳。 陆婆平日最是惧怕儿子,哪敢说半个不字,连忙说:“等我脱了衣服就来帮你。” 说完进屋,将篮子放好,脱外衣时,把那红绸包儿落在地上,竟浑然不知,转身去厕所净手去了。 这一幕刚好被跟进屋来的陆大胆看得分明,以为是包银子,并不道破,拾起来走到外面,打开一看,却是一双精巧的绣花鞋儿。 不禁喝一声采:“谁家女子,有这般小脚!”把玩了一会,心中揣测:“这个小脚女子,必定有些姿色!只是一双旧鞋,居然用绸儿包着,搞得这般珍贵,其中必有缘故,不知为何会在母亲身上。” 当下胡乱包好,揣在怀里,脸上不动声色,打算找机会诈一下母亲,套出实情。 陆婆准备停当,出来帮儿子缚猪杀了。 进屋穿回衣服,一摸袖口,才发现那红绸包儿不见了。 当下急得叫天叫地,到处寻找,陆大胆冷眼旁观,等了好一会,方才不紧不慢走过去问。 “什么东西丟了?急成这个样子!” 陆婆不敢说实话,只推说是一件要紧物事。 “你老人家目力不济,给我说个大概,或许能给你寻得着,你老人家要是不愿说,我也就爱莫能助了!” 陆大胆阴阳怪气地说道。 见儿子话里有话,陆婆忙问:“是不是你捡到了,是的话,赶紧还我,有许多银子在上头,够你花销好一阵了!” 听说有银子,陆大胆心动不已,只是有其母必有其子,面上并不表露出来。 “东西倒是我捡到了,只是你得把根由告诉我后,才能还你!” 陆婆无奈,只得将儿子叫到里边,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。 得了消息,陆大胆眼睛骨碌一转,假意惊呼:“幸好告诉我见,差一点出大事!” 陆婆见他一惊一乍,忙问:“此话怎讲?” “老话说得好,若要人不知,除非己莫为,这种事,早晚都要暴露,你当潘杀星那个老强盗,可是好惹的么?到时知道是你在中间作鬼,只怕我们两人身家性命都不保!” 被儿子一吓,陆婆慌了神,当下准备出门,要把银子和鞋儿还给柳欢,撂挑子不干了。 陆大胆拦住母亲,将她手里的银子收在自家袖子里,说:“这银子和鞋儿切不能还他,万一日后他在别处弄出事来,连累到你,拿出来也可以做个见证。要是没事发生,自是最好,银子落得受用,谅他也不敢来讨!” “倘若柳公子来问回音,该如何是好?” “你老糊涂啊!就推说潘家门户紧,不可心急,等有机会时,自会去通报。如此回他数次,自然也就心冷不来了。” 陆大胆开始不耐烦,语气也生硬起来 银子鞋儿都被儿子拿了,陆婆不敢去讨,又听出他语气不好,再啰嗦下去怕是要发作,便不再开口,默认了陆大胆得说法。 且说这陆大胆,将自己老母亲耍得团团转,得了二十两银子,沾沾自喜,溜到街上,给自己里里外外置办了几套华丽行头。 待到第二天夜里,看陆婆睡熟了,换上新买的衣衫,打扮一番后,取出鞋儿藏在袖里,反锁了大门,摸黑来到潘家楼下。 当夜并无月色,漆黑一片,且喜夜深人静。 陆大胆在楼下轻咳一声,不一会,果然从上而下,垂下一条布带来。 心中暗喜,撩衣上前,双手挽住布带,两脚蹬在墙上,一步一步往上爬,顷刻已到窗边,轻轻翻身进了屋子。 喜儿见人进了屋,赶忙把布带收起,将窗户掩上。 陆大胆将她一把抱住,黑暗之中,那辨得真假,喜儿只当是那少年公子,也不推拒,两人宽衣就寝。 到了四更天,依旧扯着布带从窗外溜了下去。 自此之后,只要不是明月当空,又或者下着大雨,陆大胆每夜必来。 如此往来约有半年,喜儿不知不觉中,总会漏出些马脚,潘家夫妇心中疑惑,数次盘问,喜儿只是咬紧牙关,只字不吐。 这晚,陆大胆又来了,欢好过后,喜儿对他说:“不知道爹妈是不是察觉到了,盘问了几次,都被我搪塞过去。如今防范愈严,万一被逮到,你我都不会好,今后你暂且不要来,等过了这阵子再说。” 陆大胆口中应承,心中不以为然,此时已近四更,遂起身溜下楼去了。 当夜潘父朦胧中,听得楼上有人低语,竖着耳朵要听个仔细,没曾想竟又睡去。 醒来后懊恼不已,说与浑家听,浑家也说:“我也有些疑心,但不知怎么上的楼,难道是什么神仙鬼怪,来无影,去无踪?” “管他是什么!如今少不得打她一顿,拷问出实情来。” “不好!就这么个女儿,打伤着了怎么办?如今我有一计,如此这般,看夜间有何动静,便知分晓。” 潘父听后,点头同意! 当天吃过晚饭,潘父对喜儿说:“今后你搬到楼下睡罢,我和你母亲住楼上。” 喜儿心中有事,只是暗暗地叫苦,不敢违拗。 当夜就互换了卧室,上楼前,又将女儿房门锁了。 到楼上对浑家说:“今夜要是有人来,拿住了,只做贼论,当场结果了他,一来,保住女儿名声;二来,只有如此,才能出我胸中这口恶气!” 潘母点头称是,两人凝神戒备,只等捉贼。 那知一连数夜,风平浪静,鬼影都没见着一个,心中开始动摇,心想莫不是冤枉女儿了,警惕性也日渐放低。 话分两头,且说那夜喜儿叮嘱过后,陆大胆虽心中不悦,却也耐着性子暂时不去。 过了十来天后,再也按捺不住,只想着去楼上欢好。 临走时,担心被人捉住,顺手在腰间别了一把杀猪刀。 到了潘家楼下,依旧咳嗽,等了半晌,毫无动静,只以为喜儿没有听见,又咳嗽几声,还是没有回应,便疑心喜儿是睡着了。 当夜在楼下折腾了许久,悻悻然回到家里里,心中自我安慰:“这么久没见面,她那知道我今夜会去,此事也不能怪她了。” 第二天晚上,又来到楼下,依旧无功而返,泼皮性子起来,心下便有了三分怒火。 到第三天晚上,在家喝了个半醉,等到夜深人静,扛了一架木梯,来到潘家楼下架好,也不打暗号,爬到窗边,拉开窗户翻身而入。 且说潘氏夫妇,一连在楼上住了十几夜,老鼠叫都没听到一声,心中早已动摇,疑心自己错怪了女儿,提防便懈怠了。 当夜老两口也对饮了几杯,喝了个昏昏沉沉,相互搀扶到楼上睡下。 故此陆大胆搭梯上楼,开窗时分明吱呀作响,两人却一概不觉。 是以陆大胆摸到床边,正要宽衣上床,隐约听得是两个人的呼吸声,瞪大眼睛仔细辨认,黑暗中,依稀可见是两人相拥而眠。 当下妒火中烧,以为早前喜儿说的话,是因为有了新欢,有意撇下他的说辞。 暗骂一声:“难怪接连几夜不睬我,原来是勾搭上别人,所以才故意装睡,如此无情Y妇,留着做甚?” 于是从腰间抽出利刃,无声无息,害了二人性命。 喜儿自从换了卧房,夜夜担心情人再来,好在一连过了十多日,没什么事发生,就连父母对她也宽松了些。 这天一觉睡醒,在屋里等到中午时分,还不见父母来开门,心中奇怪。 事也凑巧,前夜门锁坏了,父母只是在门上贴了封条,喜儿虽然知道,但也不敢擅自开门。 又等了一个多时辰,在屋里喊了半天,仍不闻父母答应,只得硬着头皮拉开房门。 见楼下异常安静,不见人影,遂去楼上找父母。 上得楼来,一眼瞧见父母惨状,当场吓得晕倒过去,好一会才苏醒,哭哭啼啼跑到楼下。 却又不便抛头露面,只得站在门后喊道:“各位高邻,不好了!我爹妈不知被什么人杀害了!” 连哭带喊,早惊动了附近邻里,拍开喜儿家门,问她:“你爹妈睡在哪里?” “他们睡在楼上,昨晚还好好的,今早迟迟不来开门,我上楼去看,才知……” 回想起父母的惨状,喜儿泣不成声,说不下去了。 众人听说是在楼上,就都往楼上跑去,果然见潘家老两口躺在血泊之中。 出来命案,非同小可,当下引了喜儿去报官。 可怜喜儿从未出过门,今日事出无奈,只得用头巾将脸包了个严实,就露出一双眼睛,锁了房门,随众人往杭州府去了。 不管什么年代,这种事情都传得很快,所以这一干人还未到府衙,市井中就传得沸沸扬扬了。 陆大胆已听人说了,晓得自己杀错了,心中后悔不已,在家里坐立不安,焦头烂额。 知子莫如母,陆婆向来也晓得儿子一些踪迹,结合今天的情形,料想杀人一事,和他定有牵涉,只是不敢过问,却也心怀鬼,只好缩在家里,不敢出门。 正是:理直千人必往,心亏寸步难行。 再说众人领了喜儿来到杭州府,正值太守坐堂,一齐进去禀道:“今有关子巷潘家,夜来门户紧闭,夫妻俱被杀害在楼上卧房,我等领了她女儿喜儿,特来禀告老爷。” 太守听是命案,当即唤喜儿上前,仔细盘问,喜儿一一答了。 “门户未开,东西也没丟!”太守也有些疑惑,想了想,问喜儿:“你家可有仇家?” 喜儿只是摇头。 太守一时没了方向,沉吟了半晌,方才开口,命喜儿抬起头来,见她把脸包得严实,吩咐她揭开头巾。 除了头巾一看,果然美丽不可方物,心想此案八九不离十,是因色而起了。 遂问了喜儿年龄、婚姻状况等个人信息,得知她原本睡楼上,父母不久前才和她对调卧房,太守眉头一皱,喝到:“是你自个儿杀了双亲!” 当场吓得喜儿魂不附体,哭着辩解:“大老爷在上,他们是我的生身父母,我岂能做出这等大逆不道的事来!” “不是你杀的,那就是你的心上人杀的,赶快将他名字说出来!” 闻听此言,喜儿心下慌乱,只还心存侥幸,强作镇定说:“我向来足不出户,邻里都可以作证,如有这些不三不四的事情,邻里岂能不知?老爷只要问他们,便知我平时为人了。” 太守怒道:“你父母双双被害这样的大事,如若不是你通知,邻里尚且不知晓,偷情之事,邻里又如何得知?此事分明是你与奸夫往来,被父母察觉,故此半月前才和你对调卧房,没曾想因此绝了奸夫的门路,导致他激愤杀人。要不然,你且说说,为什么要换你到楼下睡?” 原来,古时候,未出嫁的女儿,一般都是养在楼上,若无特殊情况,不可能父母住楼上,女儿反倒住楼下的,太守抓住这个疑点,旁敲侧击。 常言道:“做贼心虚。” 喜儿被太守句句说中心事,不觉脸上红一阵,白一阵,口里语无伦次,话都说不清了。 见她这副模样,太守已是有了七八分把握,吩咐左右用刑。 早有皂隶飞奔上前,扯出喜儿手来,套上夹棍,那细皮嫩肉,怎经得住,连忙求饶:“大老爷,有,有,有奸夫!” 太守让众人停手,看她有何话说。 “那人叫柳欢!”喜儿再不敢隐瞒,将两人如何看见,如何勾搭上,又如何上的楼,全部详细交代了一遍, “恳请大老爷明察,我说的都是实情,只是爹妈被害一事,确实不知。” 说罢叩头不止。 太守见她招出奸夫,当即差四个皂隶速拿柳欢来审。 四人领命,飞奔而去! 此时柳欢正在书房中闷坐,有家仆来报,说来了四个公差! 当下也吃了一惊,不知所为何事,到客厅相见,问其来意,公差只说,到了便知。 只得换了身衣服,心里打鼓,跟着四人往府衙去了。 正是:人在家中坐,祸从天上来。 走在路上,便听得一路上有人在传:关子巷的潘喜儿,伙同奸夫害了爹妈,绘声绘色,如本人身临其境! 柳欢听了个真切,心中惊骇,暗道:“看不出这丫头,居然是这种货色!幸好与她未成事,不然非得缠在这是非之中。” 不一时,来到公堂,太守将柳欢上下打量一遍,见是个文弱公子,不像是个杀人凶徒,心下有些疑惑。 脸上不着痕迹,喝问:“柳欢,你谝奸潘喜儿,为何又将其父母杀害?” 那柳欢乃风流子弟,行奸卖俏,玩耍风月,才是他的专长,何曾见识过官府的威严。 公差去他家时,就已是胆战心惊,如今闻听潘喜儿父母被害的事,落在自己身上,犹如晴天一个霹雳,吓得魂飞魄散。 半晌回过神来,大喊冤枉:“禀老爷,小人与潘喜儿虽然有意,却还未能成奸。切莫说害他父母,就是那楼上,我也从未上去过。” “潘喜儿已招认,说与你通奸已有半年之久,还敢抵赖!”太守声色俱厉:“如若你不是凶手,你又为何强调未曾上过楼?” “小人来府衙的路上,都在传闻此事,是以知道她父母被害在楼上!” 转头又对潘喜儿说:“我什么时候与你成奸了,为何要害我?” 潘喜儿起初也不确定父母是不是奸夫所害,如今见柳欢矢口否认两人奸情,也疑心起命案真是他所为,遂一口咬定,哭啼不休。 柳欢有口难辨,太守喝教夹起来。 只听得两傍皂隶一声吆喝,蜂拥上前,套上夹棍用刑。 可怜柳欢从小锦衣玉食,如何受得了这个,夹棍刚套上,就杀猪般喊起来,大叫愿招。 太守命皂隶住手,让柳欢写供状。 柳欢边哭边说:“我并不知情,却叫我怎么写?” 只得看着潘喜儿说:“你不知被谁骗奸了,却把我扯来做挡箭牌!罢了罢了!如今也不消说了,但凭你说,我就依你的口供招认便是了。” 见柳欢到现在还不肯承认两人有染,潘喜儿也恼了,责问:“难道你没在楼下调戏我?难道那汗巾不是你丟上楼给我的?难道我的绣花鞋不是你得了?” “这些倒都是实情,只是我并没有上楼与你相处过啊!” 太守在堂上听得分明,喝道:“一事真,件件真了。休要闲扯,快快招供!” 柳欢只得闭口,听潘喜儿说一句,他写一句,将死罪认在身上,画供已毕,呈与太守。 太守当场判决,将柳欢问实斩罪,喜儿虽不知情,因奸情害死父母,也与柳欢同罪。 各打了三十大板,分别收监。 也就是柳欢有钱又阔绰,四个公差去他家时,就分别封了红包,所以虽然挨了三十下板子,却是看着吓人,实际没什么损伤。 一干皂隶和狱卒,将他当成财神爷供着,刚收入牢房,都来问他:“柳公子,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?” 柳欢苦笑:“不瞒各位大哥,我虽与那潘喜儿有意,但真未能成事!不知是什么人做的,却把我拿来顶缸!各位看我这个样子,像是个杀人的么?” “那你刚才为什么招认?” “能有什么办法,就我这身子骨,熬得住那刑罚么?招了,还能多活几天;要是坚持不招,这条性命兴许当场就送脱了!也是我活该倒霉,但那潘喜儿说起私通之事,不像有假,其中肯定有问题,烦劳各位帮个小忙,带我去见见潘喜儿,我愿拿出十两银子,请各位大哥吃杯酒。” 狱卒头儿上前一步说:“要看见潘喜儿也不难,只是十两太少了点。” “那就在加五两!” “我们人多,分不来,最少也得二十两。” “成交!” 当下走出两人开了牢门,一左一右扶了,径直来到女监门外。 潘喜儿正在里面哭泣,抬眼看见柳欢,开口就骂:“你这没良心的贼!我一时被你迷惑,与你相好,对你到底有什么亏欠,你要下如此毒手?” 柳欢赶紧低声劝慰:“先不要嚷,我来见你,就是要把事情弄清楚,听我讲完,兴许还能找到害你爹妈的正真凶手。” 潘喜儿见他表情诚恳,也有些犹豫了,便耐着性子听他说。 前面的事,两人说法一致,柳欢就从请陆婆传信开始讲起。 那日他托付陆婆后,就去一个相好那里住了三天,回家后得知婆子来卖过花,心想是来回消息的。 于是返身出门去找陆婆,那婆子却告诉他,说鞋子给了喜儿,因潘父防范甚严,无法可想,好在一段时间后,潘父要出门半年,到时才可大胆相会,叫他耐心等待。 柳欢信以为真,就在家等着,那知日复一日,并无确信,竟因此相思成疾,叫了郎中开了方子,服药调治,一直到前几天,才稍稍调养好一些。 柳欢讲完,叹息一声说:“如果我真的与你相处了半年,体型声音,必定熟悉,你且认真审视,看看我是与不是?” 喜儿也踌躇起来,上上下下打量着柳欢! “快说,到底是不是?不要迟疑。”柳欢追问。 “声音不像,体型也不像,只是向来都是黑暗中见面,实能分辨,只记得你腰间有个铜钱大小的疮疤。” 一旁众狱卒说:“这就简单了,柳公子,且把衣服脱了一看,要是当真没有,明日禀知老爷,我等给你作证,帮你洗脱罪名。” 柳欢满心欢喜,先谢过众人,当下褪下衣服。 众人一看,遍体光洁如玉,腰间哪有疮疤? 喜儿顿时哑口无言。 次早,太守升堂,众狱卒到堂上跪下,将前夜柳欢与潘喜儿面证之事,一一禀知。 太守大惊,当即将两人提出牢房再审,先问柳欢,从头至尾,又细诉一遍。 又问了喜儿,喜儿也把前后事,再细细呈说了一次。 太守略一沉吟,说“陆婆告诉柳欢,说鞋儿被潘喜儿收去了,潘喜儿又说,是奸夫给她的。看来,问题就出在这双绣花鞋上了!” 当下差人去拿陆婆来问话。 不多时,婆子拿到,太守责她帮人私通,先让人打了四十大板后,方才问话:“当初柳欢托你与潘寿儿通信,给了你一只鞋儿,你与潘喜儿见面后,她也给了你一只,凑成一对儿,你却为何哄骗柳欢,说鞋儿给了潘喜儿?实情是你将鞋儿给了他人,以此为信,冒名去奸骗!一五一十速速招来,如有半句虚言,当场打死!” 那婆子被这四十大板打得皮开肉绽,只剩得半条命,哪敢还有半分隐瞒,便将鞋子如何落到儿子陆大胆手中,前前后后,详细交代了一遍! 如此一来,前后印证,太守心知奸夫定是那陆大胆了,当即又差人去拿。 不一时,陆大胆押到,初时还想抵赖,只是刚一开口,潘喜儿就喊道:“禀老爷,我认得这个声音,谝奸我的,正是此人!他左腰有个疮疤,一验便知!” 左右皂隶剥下衣服看时,果然有一个铜钱大小的疮疤在左腰上。 陆大胆自知事情败露,颓然瘫坐在地上,为免受刑,老老实实,全盘招供了。 至此,此案终于大白! 太守当堂给众人定罪:陆大胆谝奸杀人,问成斩罪,先打八十大板;喜儿维持原判,也是斩罪;陆婆收人财物,诱骗良家女子,下入牢房;柳欢见色起意,企图行奸,虽未成事,但本案因此而起,实为祸端,亦下入牢房! 判决已毕,众人心服口服。 只那潘喜儿,今日见了陆大胆,才知自己把个冰清玉洁的身子,给了如此粗鄙不堪的屠夫,还害得父母双双丧命,羞愧难当,竟咬舌自尽了。 众人发觉后,唏嘘不已,太守心中不忍,又让人打了陆大胆二十大板,下到死牢,等候问斩! 命差役找来潘家邻里,吩咐将潘家财产变卖,备棺盛殓了一家三口安埋,余银入官上库。 柳欢想到潘家一家三口,都因自己而死,自责不已! 使了些钱财,免了牢狱之灾,谢过了公差狱卒等人后,亲自到僧房道院念经超度潘家三人。 自此以后,立下重誓,再不染指别家妇女,就连花柳之地,也再未踏足! 后记: 文中潘喜儿的命运!让人可悲可叹!皆因年少无知,轻易被人诱骗,贪一时欢好,最终连累父母,自己也用年轻的生命为自己的行为买单! 柳欢这种人,着实让人讨厌!仗着自己有钱,为所欲为,见到有姿色的女子,就想据为己有,就因为如此,差点吃了人命官司,好在最后迷途知返。 陆氏母子,皆是罪有应得! 故事内容为虚构,旨在导人向善!劝各位慎之戒之! 配图来自网络,侵删!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daoshuilian.com/yhhdsl/11056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电视剧红楼梦展示的中国古代家具匠心独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