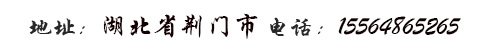杜孝玺滕州ldquo十大碗rdqu
|
提起“十大碗”,各地人都眉飞色舞、如数家珍地述说各自家乡、各自心中的家乡美味,一如说起家乡的山、水、人、情。乡愁的滋味,更是舌尖上家乡年少时的味蕾记忆,更行、更远、更惦记。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方人成就一方美味。“十大碗”是共同的乡愁话题,“十大碗”碗中的菜肴却因地因时因事而不同,既有就地因时取食材,又有因红白喜事和贫寒富足而就事论事,因此“十大碗”地地相异、家家相异、事事相异,是大同小异。东营肉多且盘子大,透着石油老大哥的豪气与凭海临风的大气;枣庄羊肉汤、辣子鸡厚重实惠,体现的是煤城包容融合的和气;曲阜每道菜文雅端庄,“诗礼银杏”“带子上朝”“一品素锅”“书箱豆腐”,蕴涵着儒家的书香气……一说“十大碗”,那肯定是自己家乡的最好吃。滕州“十大碗”,是我心中永远的第一,连着母亲的味道和老家的烟火,还有那温暖的记忆和记忆中温情的故事。小时候,农村都穷,城里人家也不富裕。年幼的我们正是长个子的时候,吃嘛嘛香而又很少能吃到好东西,最盼望的就是亲戚本家有个红白喜事,凑个热闹不用干活,还能吃上大席。吃大席也叫坐大席,最早时真是在地上铺席,人坐席上围坐一圈进食。铺上席即是别于席地而坐,铺席是敬礼。古时通常是坐在地上吃饭的,就像三夏三秋大忙时节在田间地头吃饭,因陋就简;铺上席就郑重且排场了,肯定席上的菜肴也不一般。民间只有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才是大事,又被婉称为红白喜事,一有红白喜事就能吃大席或坐大席,所以吃大席或坐大席就成了办大事的代名词。大席主要以“十大碗”为主,丰俭随主家心意,个人根据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定丰盛或节俭。滕州“十大碗”一般有扣碗江米鸡、扣碗鱼块、小酥肉、莲子银耳汤、扣碗丸子或四喜丸子、扣碗千子、扣碗酥山药或地蛋、扣碗酥瓠子、两个时令风味炒菜,菜品荤素搭配,扣碗中多以黄花菜或绿菠菜相衬,既好看又显得菜丰满,营养搭配也算合理,老少皆宜,风味独特。大席丰俭的表现一是在盛菜碗盘的大小上,再就是在菜的内容上。有的一半是青菜或黄花菜作衬底,酥菜或肉很少,一浇汤飘起来,乡邻称之为“漂汤菜”,要被人暗暗地议论老长时间,一遇大事就会提起,甚至有的都影响了儿女说媒。我就吃过扣碗酥油条,把油条裹上面糊再过油炸,特别酥、脆、香,至今记忆犹新。总以为是实在没有别的菜可过油,急中生智,用油条顶一样,硬凑合的。后来在潍坊寿光吃到油条调黄瓜,先以为是早上剩的油条没吃完,中午废物利用。晚上换了家饭店,头一道凉菜又是黄瓜调油条,才知道是当地名吃。再后来,又在济宁吃过酥油条,听说徐州也有这道菜,暗笑自己的眼界小见识少,佩服厨子的匠心独运。遇到红白喜事设宴待客,就得聘请厨师。民间称厨师为“厨子老师儿”,是一种半职业半业余的性质,平时种地或开小饭馆,有事时由事主发帖委托人去请。干红白喜事宴席的厨师是踩百家门的,可上门服务;开饭店、菜馆的厨师则坐店等客不踩百家门。这是祖师爷“太上老君”定的规矩,一日入门,终身遵守。喊“厨子”,厨师不高兴,厨子整天烟熏火燎,浑身油腻,又是伺候人的活,最担心别人不尊重看不起,一不高兴就会在菜的火候和味道上给你使点奸,让你吃点苦头他好找点心理平衡;若喊“厨子老师儿”,则高兴,凡事百顺听招呼。小时候,写喜帖的老私塾先生看我听话且伶俐,教我喊“厨子”为“俎匠老师”,说商朝宰相伊尹当过厨师,能“调和鼎鼐,燮理阴阳”、“治大国若烹小鲜也”,厨子听后喜得不撑天,两眼放光,要嘛给嘛。只是“俎匠”的雅称,很少听闻,多次与人讨教“俎”还是“焗”,争论无果。厨子工作主要在案板上切割斩伐,窃以为“俎”字为宜,古而雅且切题。厨子接帖后要到事主家去做相关准备工作:拉菜单、采买、支灶、破菜、过油、吊汤。过油就是炸酥菜,鱼、肉、山药或地蛋甚至油条,挂上面糊在热油里炸。鱼肉金贵,主家艰窘,买的少,厨子接了活就得把场圆下来,只能把面糊活稠,小肉丝、薄鱼块勾上厚厚的芡,油锅一炸,也是酥菜,浪得一名,人称“面疙瘩”。吊汤更是技术活,“唱戏的腔,厨子的汤”,汤吊的好坏决定了厨子的水平,关乎名声。吊汤要选两年以上的老母鸡煮汤,开水下鸡,旺火沸煮两小时以上,达到微黄浓汤。汤煮好后盛入瓦缸内,撇去鸡油,算是通用高汤。临上桌时根据咸辣酸淡,再滴入花椒、葱、姜熬制成的葱椒油。滕州“十大碗”是开席前装碗上笼馏,酥鱼块、酥肉码碗,碗面要码放整齐,垫衬菜也要放好,上笼馏要大火足气,馏出来的菜品要达到酥软糯烂而不失其形。揭笼时趁热扣上大碗,上菜时再迅速将扣碗反转,适量加入调好的高汤,酥菜外软内酥,高汤恰恰入味,尤其扣肉碗面鲜美光亮鼓如馒头,埋在下面的黄花菜或地蛋块味道更是堪比五花肉啊。可惜的是,现在再也吃不到那个味了。红白喜事都是“十大碗”,可内容不一样,吃法也不一样。红喜事是文吃,时间长,礼数多,上菜慢。入席讲究主、陪,上菜讲究“一鸡二鱼三丸子”,有最后上辣子鸡的,也有最后上鱼的,扫尾,吉庆有余,鱼上完了,就上饭,所以有“跟着大鱼上饭”的说法;也有最后上丸子的,取其圆满之义,一挖丸子,即近尾声,曲终席散,故有“滚蛋丸子”之说。反正第一个菜是雷打不动地上鸡,大吉大利,吉星高照。鸡上来,有经验的人都不动筷,主家长辈来“稳菜”,象征性地把鸡端到主宾面前,一番“房浅屋窄、酒薄菜孬、包涵担待、多用几杯”的客套说辞,也叫整席。整席后,则开喝。一人一个酒瓯子,盛三钱三酒,俗称“牛眼瓯”,一桌一把酒壶,客客气气,文文款款,让半天,喝几次,才干一瓯。让菜更是三番五次,要么不动筷,动筷也是浅尝辄止,真给当客的样。我家就我一个男孩,常参加出头露面吃大席的场,父亲每回都教待:要“有人样”,要别人捯菜你再捯,别人停筷你就别动了,嘴是过洞,多吃一点长不起鼻洼来……母亲干脆就先让我在家吃个半饱再去坐席,免得没“人样”,被人笑话吃相不雅。邻家大哥是个出力汉,在山上开石头,人朴讷不善言辞。新婚后去岳丈家拜年,陪客的让酒劝菜,他一律回答“剩不下”。年轻饭量大,家里人忘了专门教待,又不会客气作假,果然风卷残云,菜饭剩下不多。以后再走老丈人家,小舅子妻侄都喊他“剩不下”。再就是当客不能随意乱说话。一家新娘的哥哥是城里的干部,当叫头趟回门的大客,吃席时在乡下吃到凉拌海蜇,一高兴,随口说:“这菜不错,再来一盘。”他是城里人,不懂农村规矩。主家可就抓瞎了,菜是般般和好兑乎成的,计划经济年代,又是偏僻山乡农村,上哪再弄一盘海蜇去呢?大红总灵机一动,让新娘去给他哥悄悄解释,他哥说:“什么海蜇,我早忘了!”后来吃饭“这菜不错,再来一盘”成了典故,一说大家哈哈一乐,都知说谁。酒过三巡,菜过五味,主桌的主客要赏厨,拿出事先封好的红包,交给端大盘的送给厨子。不赏厨,厨子就要刁难,不是迟迟不上菜,就是菜里多放盐或不放盐,让你咸里闲(咸)吃淡里蛋(淡)吃,行话是“被卡勺子头了”。也有主家安排厨子不收赏厨,最后主家一并结算,主客就要拿两盒好烟,由主陪、副陪陪同到厨房向厨师客套酬谢一番。菜快上齐,主客就请求辞酒上饭:天也不早了,酒也喝好了,酒待客,饭也待客,饭后回去还有老远的路,请上饭吧!陪客的则以“一脚丫子地,抬腿就到,天还早呢,再拉会呱,再喝气酒”等言语推辞上饭。主客再以“酒无尽,话无尽,来日方长,以后再叙”再请上饭。如是者三,撤酒上饭。吃饭又是一番推让。饭一般是馒头,取其生发圆满之象征,且顶上点红花,喜庆。以前生产队挣工分,小麦产量低,户家分到的小麦少,过年吃顿白面饺子都难。在新客拜年的大席上,一桌八人,有一家仅上了六个馒头。会圆成的主陪灵机一动,把一个馒头掰成两半,半个馒头往主客新女婿手里一塞:“他姑父,您受,也得受这半个!”本以为这一招化解六个馒头八个人的僵局,哪成想新女婿酒喝的有点高,又没大吃菜,正饥肠辘辘,实诚地答复:“就是今天撑死我个妻侄,我也得吃一个喜馍馍。”酒足饭饱,撤席上茶。茶一倒好,明白的主客立刻辞别,主陪再四挽留,最后众人依依惜别,讲究的送到村外,不讲究的也得送到大门外路口处。屡次回头,屡次挥手,渐行渐远,礼数方成。白事的“十大碗”也叫“喝豆腐汤”,是武吃,抢席(西乡也叫“抢座”)。因为时间紧,前客要让后客。坐席前,执事已领孝子在大门外客棚前举行过“高座礼”,孝子向各方跪拜,意思是请各位亲朋高座,也就是坐哪里哪里就是高座。坐席时,留出当门首坐的那桌,坤丧留给娘家人,乾丧留给死者的姑舅老表、外甥或女婿。其他的桌,抢哪地坐哪地,非不得已,不坐席口。因为把席口要负责接菜拿饭,而菜一上来,就风卷残云。白事上菜还快,真是应接不暇,若是把席口人不老练再加上吃饭慢,恐怕只能是残羹冷炙对付个半饱。有的地方还兴“砍菜”,上来一个,“我砍了”,端过去自己一个人吃,别人再“砍”别的菜。滕州人目瞪口呆地半天才明白,慌忙有样学样“这个菜,我砍了”,端上来一看,是馍馍!还好,总算有饭吃,不赖。据说东山里办白事不准备饭,仅给娘家人和姑爷备饭,其他亲友一律干粮自带。不知风俗的第一回去,只能光吃菜,看别人吃花样不一样的干粮。酒是用碗,倒满一碗,一桌人传着喝,多少随意,没人劝。一般喝不到三轮,饭就上来了,这时就用大马勺舀开水,加到菜碗中,有人往碗中泡馍馍,连饭加菜用调羹舀,连吃加喝,汗流浃背,急赤白脸,很是爽利。孝眷们到客棚行谢客礼,执客高喝一声“谢客”,孝眷们扑通一个头磕下去,情急之下,客们利索起立,齐说“免了,免了”。若是吃饭中有孝子孝妇的外甥、女婿、干儿、孙婿或闺女、干闺女、侄女、孙女、外甥女等,必须离席,就地向孝子孝妇还一个头,以示晚辈不敢?受长辈叩谢大礼。菜一上齐,执客就进客棚寒暄:“吃好了吧?前客让后客吧?”大家就络绎离席,一顿大席吃下来,前后也就半小时光景。红白喜事吃大席都要先搭客棚,安桌椅。红事,桌要八仙桌,椅最好泰山椅,怎么着也得靠背椅。白事,八仙桌外,仅要四张条凳就行。喜事(也就是喝糖茶送粥米),地八仙桌,小板凳足矣。形式与内容绝对统一,乡野智慧,尽在其中。还有就是红白事皆有鼓乐班子,唢呐笙箫锣鼓胡琴,增哀添乐,直走人心,很乡土,也很中国。礼序乾坤,乐和天地。有礼即用乐,红事礼、白事礼,行礼如仪,礼乐教化,相得益彰。礼失求诸野,一个“十大碗”就吃出如许多的文化礼教,信然。大席吃完,总有剩菜。主家以菜丰盛、剩的多为有面子。把剩下来的菜统统折到沙缸或盛过高汤的瓦缸中,我们那里叫杂烩菜,有的地方叫折菜或大席菜,用炒勺加热后,用碗分送给邻里百舍。讲究的人家,不够分时,再做点新的羼入折菜中。这是古代“散胙”遗风,只是古代祭祀完后是分祭肉,民间变成了分“折菜”,答谢办事期间邻里百舍的帮忙、桌椅板张的出借。收到折菜的人家,日后见到主家又免不了一番道辞。人情便在这一来一往中又醇厚了一层。饭局中常常说起小时候的大席菜,似乎特别香特有味,与我同龄老家在农村的都有同感,便相约去“大席菜饭店”专吃大席菜,似乎缺工少料,吃不出当年的味道。我想起相声中说的“朱洪武皇上的珍珠翡翠白玉汤”,课文中学的《芋老人传》,世易时移,物是人非,乡愁而已。滕州“十大碗”,一个值得回味的话题,一缕永恒不去的乡愁。家乡烟火,风物可亲。杜孝玺,年生于山东滕县,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。滕州市政协副主席,曾任滕州二中语文教师、乡镇干部、滕州市教育和体育局局长等职。热爱文学,擅长文史。 善国文化讲好滕州故事
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daoshuilian.com/hhdslzz/10490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60道煲汤不放肉的素食汤谱,不仅营养还出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